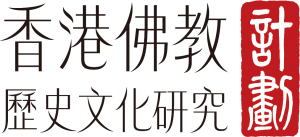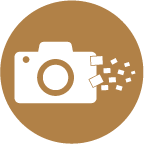倓虛老法師來港 創辦華南學佛院──弘法精舍歷史再考(三)

弘法精舍八十多年來,一直重視為佛教、為社會培育人才。精舍的創辦人黃杰雲居士夫婦,即使在戰事期間,仍計劃將來如何推動弘法工作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正式向盟軍投降,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。
弘法精舍雖然在這段期間並未受到戰火的無情摧毀,但自從抗戰勝利後 ,一直空閒,無人居住。百廢待興,不少事情須重頭來過。黃居士夫婦見到莊嚴道場受戰亂侵擾,荒廢數年,實有違他們的弘法心願。幸好有時任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及董事長王學仁居士相助,依照東蓮覺苑方規,成立保管董事會,負責主持精舍此後的弘法大計。他們四人共同管理精舍,又向各方奔走,籌措經費,著手開辦新的佛學院。
1949年春天,香港佛教界收到消息,來自東北的倓虛老法師要南下,這對大家來說是天大的喜訊。

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,旨在注重行持
倓虛老法師(1875-1963,下稱倓老),河北省甯河縣人,俗姓王,名福庭 ,生於1875年。倓老中年前行醫為業,交遊廣闊,始知有佛法,而其後求法之心益切,自行研習經論。在四十三歲那年,他前往天津清修院求清池老和尚剃度。老和尚見其相貌,知他日後必成大器,故不願受他執弟子之禮,並引薦他至河北省高明寺純魁法師處。純魁法師為其剃度,賜法名隆銜。後來倓老得知寧波觀宗寺諦閑大師之門下弟子,為慶祝師父六十壽辰,故安排了傳一堂戒。於是他把握這個機會,報名參與,依諦閑大師受具足戒,獲賜名倓虛。倓老後又入讀觀宗寺佛學研究社,一次因覆講而得大師贊許,評他為「虎豹生來自不群」。他此後追隨諦閑大師到處弘法,並獲傳授天台宗法卷,為第四十四代傳人。
倓老堪稱近代佛門泰斗。他在中國東北、西南各地建立道場,致力振興佛教,如青島湛山寺、遼寧營口的楞嚴寺、哈爾濱的極樂寺,及吉林長春的般若寺等。 他一生又主辦過九家佛學院,其門下弟子不可勝數。[1] 1949年,倓老仍駐錫湛山寺。據其弟子樂渡法師憶述,時局有變,青島市面人心惶惶。湛山寺諸位護法及方丈善波法師與他商量,虛雲老和尚與葉恭綽居士 [2],來函邀請倓老,南下廣州重修光孝寺一事[3],著法師先往香港和葉居士接洽。關於倓老駐錫香港,及於弘法精舍辦佛學院的經過,有以下幾種說法:
一、樂渡法師先往香港,尋找葉恭綽居士。1948年底,法師由青島抵達上海,再乘火車前往廣州六榕寺。同行者有達成、性空、聖懷、智開、永惺共五人。樂渡法師會見葉居士後,言明倓老有意南下弘法,十分歡喜,於是邀王學仁、林楞真、黃杰雲、王璧娥、樓望纘諸居士商議。眾人一致歡迎倓老來港弘法,兼辦佛學院。弘法精舍諸董事亦同意借出地方為院址。
樂渡法師與葉居士分別致電催請倓老來港。1949年4月1日,倓老由青島抵達上海,4日由上海飛抵香港[4]。倓老到埗後,香港佛教界仝人紛紛到機場歡迎,接風洗塵。第二天,倓老與葉居士會晤,議決創辦僧校,定名為華南學佛院。葉恭綽、王學仁、黃杰雲、樓望纘、林楞真五位居士為學佛院護法董事,倓老任院長兼主講[5]。(樂渡法師說)


三、弘法精舍戰後幸得王學仁、林楞真兩位居士襄助,依照東蓮覺苑方規,成立保管董事會,負責主持一切大計。董事會於是開始選聘高僧,以擔任領導地位,開展弘揚佛法的工作。1949年,倓老駐錫青島湛山寺,經葉恭綽居士的推薦,提請董事會通過,轉請佛教聯誼會(即香港佛教聯合會),代發電報邀請來港,主辦華南學佛院[7]。(倓老說)
綜合來說,倓老因局勢變動南來,香港佛教界仝人聞訊,歡喜至極。剛巧弘法精舍諸位居士有意籌辦佛學院,因緣和合下,與之洽談留港弘法事宜。倓老逐決定駐錫精舍,辦華南學佛院。
至於為何稱「學佛院」而非「佛學院」,倓老在呈交香港佛教聯合會的備案上說得很清楚:
「竊以佛法真諦,端在行持,教義流傳,賴諸弘揚。自民國以來,各地佛學院,如雨後春筍,莫不宏揚佛教,培養僧材為職志。其目的無非為令正法久住,教義普及,破無始之執迷,啟原有之正信。查本港於民國二十八年間,曾創有弘法精舍。請已故寶靜法師為主講,招收有志學僧,造就弘法人材,厥功至偉。後以因緣失調,未能垂續,弘法精舍遂告終止。今年春間,港中熱心佛教之居士,發心創辦佛教教育,繼續培植人材,以符弘法旨趣,地址仍假前弘法精舍,並定名為華南學佛院。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,旨在注重行持。於佛法奧妙中有真修證,有真受用,以期將來,宣演聖教,淨化人心,賡繼佛法慧命,闡揚大乘精神。倓虛辱荷諸居士,推為院長,承乏院務,現已招收學僧二十一名開始上課,經費暫由諸居士等籌措,以俟稍為就緒,院內學僧,實行工禪制度。即半日工作,半日學法,以期達於自給自足之程度,竊以 鈞會為本港佛教最高機關,凡屬佛教團體,均在管轄之內。除已呈請 香港政府備案待予批准外,用特具文呈請,仰祈 鑒詧准予備案,實為公便。 謹呈 香港佛教聯合會。院長倓虛謹呈。」──〈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.鈞會准予備案由〉[8]
倓老特別強調行持這一方面;他期望入讀的學僧,能夠有真正的修行和體證,將來學以致用,淨化人心。
學佛院董事會原議招收學僧十名,給予倓老每月經費港幣一千元。葉恭綽,樓望纘兩位居士擔任常年經費。王學仁、黃杰雲、林楞真三位居士,則負責借出弘法精舍。
東北三老與入讀學僧
此時,倓老又寄函給定西老法師及樂果老法師,請兩位來港相助,擔任輔講教師。定西老法師(1895-1962,下稱定老)生於遼寧,俗家姓名于澤甫;樂果老法師(1884-1979,下稱樂老)也是遼寧人,俗家姓名陸炳南。王福庭(倓老)、于澤圃及陸炳南出家前經常相聚一起,研習出世之道。三人之中,以王福庭出家後,于澤圃亦在淨宗大德寶一老和尚座下剃度,法名如光。如光法師後前往普陀山法雨寺,依達園和尚受具足戒。定西是後來老法師來港後改的別號。陸炳南則最晚出家,當年已經是五十六歲了。他依遼寧開原市龍潭寺剃度,法名大聞,號樂果。後世尊稱三位大德為「東北三老」,以表彰他們振興東北佛教、發展香港佛教的巨大貢獻。

一些之前在東北曾經跟隨三老的弟子,亦陸續來港。例如淨真、智梵、法藏、妙境、明遠幾位法師,本來在上海浦東海會寺親炙定老,研習《法華文句記》;後來定老收到倓老請函來港,幾位年輕僧人也就順理成章跟著師父進入華南學佛院[9]。此外,又有其他年輕僧人聞風而來者。倓老為了長遠造就更多僧才,於是向董事會提出要求,增加收生名額至二十名[10]。這二十位學僧包括(排名不分先後):
樂渡、性空、大光、法藏、寶燈、永惺、妙智、達成、聖懷、淨真、圓智、智開、妙境、定因、明遠、智梵、濟濤等[11]。
華南學佛院大致上沿用倓老1940年代初,在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擔任校長時所訂立的編制[12],例如每三年為一個修業期限;期滿考試成績合格者,獲頒畢業證書;同時課程亦必須包括中文、歷史、地理等俗世知識。在這三年間,學僧要修讀的佛教內容包括法華、天台、楞嚴、止觀、唯識、淨土及各項儀軌等。根據智梵法師所言,華南學佛院所教授的課程,與湛山寺佛學院大同小異--以天台三大部:《法華玄義》、《法華文句》、《摩訶止觀》為宗旨,其他課程為輔。其中與湛山寺不同的,是多添了一門醫學──傷寒論。因為倓老懂醫,故能由他老人家觀臨指導;另有尚有蔣維喬居士講述《文字蒙求》等[13]。
開學僅年餘,學佛院要維持日常開支,逐漸變得困難了,畢竟每月一千元要應付二十六人的是開支,還是頗感拮据。樂渡法師說,倓老曾向董事會要求,每月經費增加三百元,總算勉強支撐得來。學僧又需要「每日課餘,分組種菜,上山斬柴,以補不足。」不足一年,董事會提議學僧半工半讀,以期自力更生。不過,適合學僧的工作並不多,而且董事會有時意見爭持不下,常形成僵局,苦了倓老和陪他開會的樂渡法師--「……負責經費者,要學僧半工半讀;不負責經費者,則不表同意。因此曾有短時期之僵局。至時取款不到,縱倓老親去董事會要求,亦屬枉然。艱辛苦況,真是一言難盡。」
後來倓老聽從董事會建議,買織襪機作織襪用。但奈何學僧是外行,努力下雖能順利得到一個月之收入,始終是事倍功半,實非長久之計。與此同時,負責經費的葉恭綽、樓望纘兩位居士先後離港。樂渡法師與倓老再三商量,皆因學佛院之存亡,危在旦夕,他們必須另想辦法妥善解決。
倓虛老法師為學佛院籌措經費一事,感動了上海紗廠主人江上達、楊之游等人,他們慨捐巨款,代為購置精舍電燈、蓄水池及蓄糞池等項目,無形中減輕了眾僧負擔。
莊嚴法器 水陸道場
另一方面,有一位吳蘊齋居士(1886-1962),他是民國時期的金融家,曾任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。經董事會邀請後 ,吳居士入住弘法精舍,皈依倓老,得法名「能任」,承擔了部分籌措日常經費的責任。
倓老同時又派永惺法師及寶燈法師往青島湛山寺,取得寺中莊嚴法器,以便在弘法精舍籌辦水陸法會。華南學佛院辦的水陸法會,全稱是「冥陽兩利法華水陸道場」。倓老之所以特別強調法華二字,是他相信當年佛陀在靈鷲山,最後開的是法華高會,宣講《法華經》;這是高過過去一切的法會道場。他期望佛弟子能發無上高遠廣大之心,只有這樣,方能救濟眾生。[14]
法華水陸道場每年都訂在冬季舉行,於農曆十一月十七日阿彌陀佛誕日開壇,直到農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圓滿。倓老及一眾參與法會四眾,以此功德,祈禱世界和平,戰爭永息,兼超薦諸護法過去先靈,及中外陣亡將士、災死難民、一切無主孤魂,速脫幽冥。水陸法會得到本港諸善信的支援,華南學佛院至此方解經費困憂,師生乃能逐步實踐弘法理念。

在學佛院創始初期,學僧雖經歷了砍柴、種菜、紡織等半工半讀的生活,成效依然不甚顯著,這與倓老強調出家人必須掌握一門技能,以求自身生活安定的目標,尚不少距離,於是他提出要印製其師父諦閑大師的遺集。
續佛心燈,以酬師恩
諦閑大師乃天台嫡後裔,法門龍象。倓老受大師法乳,無時不感念其恩德。大師精通三藏,說法度人無數,皆有獨到之處。諦閑大師所撰文字,過去只見於報刊,或以單行本流通,且書局隨意刊行,間有訛誤。大師示寂後,寶靜法師繼任為觀宗寺主持,葉恭綽居士其時倡議應及早編纂大師遺著,眾人推舉法師為主編,葉恭綽、蔣維喬居士為副主編。惜法師早逝,事情被逼擱置。其後倓老來港辦學,適逢葉、蔣亦同處一地,三人有感因緣和合,不能再失良機,故重提此事。倓老發願續佛心燈,以酬師恩,從葉居士處取得諦閑大師遺著原稿,花了三個月時間校對,整理出共一百二十萬字。[15]
1951年1月,華南學佛院印經處正式成立。
倓老的想法是,與其找外人去印,成本高昂,倒不如自行學習印刷。他老人家此舉,除了為使諦閑大師的文字般若以永存,更是為了讓學僧適應時代需要。因為倓老始終認為,出家人做其他工作,實屬不宜,今選定印刷一門,使佛法流通,也算是如來家業。印經處獲中華書局總經理吳叔同贈腳踏照鏡印刷機一部,又得到葉恭綽、王學仁及吳蘊齋等護法居士的贊助,購入切紙機一部,及五號鉛字。
人位方面,學佛院內共二十學僧,倓老於是分編他們為四組:

一、檢字組:樂渡、妙智、達成、聖懷、圓智、淨真、聖鐸、常安
二、校對組:大光、濟濤、法藏、定因
三、印刷組:永惺、智開、性天、智梵
四、裝訂組:寶燈、妙境、明遠、妙觀
雖然硬件已備,但對倓老及一眾學僧而言,《諦閑大師遺集》預計共十冊,約120萬字,不是一項小工程。為此他們決定先試印一些較短的講義,邊學邊做,以磨練技術。春節過後,學僧首先刊印《論念佛》。倓老在當中為大眾開示念佛的好處,並扼要說明何謂皈依三寶、八正道,雖然只有短短五頁,卻是對初機學佛很有幫助的小冊子。倓老只請來了一位印書館的熟手,抽空教導學僧兩、三次;學僧之後又到印書館參觀。此後諸事如排版、揀字、校對、切紙等,全靠學僧自學。雖然倓老認為第一次印刷的成品有不當的地方,例如行距過闊,但整體上還是頗滿意大家的努力成果。[16]
到了4月,學僧開始排印《勸發菩提心文講義錄要》,並向外結緣流通。他們的印刷技術日益進步。 5月,印經處又購入另一套三號鉛字供正文使用[17]。倓老認為學僧準備工夫已足,開始排印《遺集》。自此全體學僧,每日四小時上課、四小時印刷;後來為了加快進度,又改為每日七小時印刷,終於在9月底,他們完成了十冊其中六冊。
倓老在《遺集》後記述說師生印經的辛勞困難處,讓我們對他的慈悲宏願更加敬佩:
「⋯⋯自遺集排印開始,院內即實行半工半修,每日上午授四小時課,下午做四小時工。首用照鏡機,足蹬印刷,日出三十二開紙四頁,每頁一千篇。計將遺集印完,約需時三年。後又購雙牙四開機一部,因無電力,仍八人輪班蹬印,計每日可出四開紙一頁。五月底放暑假,為提早出版,改每日工作七小時。時逢溽暑,酷熱襲人;諸師汗流如瀋,辛勤備至!八月底暑假期滿,遺集前兩編,六冊印竣;並開始向外預約。⋯⋯」[18]
不過,倓老又考慮到《遺集》全套繁重,流通不便,於是在同年11月另行將當中的開示及講義,分訂散裝單行本,以適應及方便讀者。 例如單行本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》、《大佛頂首楞嚴經序指味疏》等,都屬於《遺集》第一部分的內容。到了年底,華南學佛院辦一年一度的水陸道場,稍稍補足了印刷費;加上頭六冊已開始接受預訂、流通,所得經款亦得以用來繼續印刷餘下四冊。
發精進心,自力修學
1952年3月23日,華南學佛院第一屆正式期滿,舉行畢業典禮。
二十名學僧中,有十名通過期末考試,順利取得畢業證書。他們分別是法藏、淨真、聖懷、大光、定因、寶燈、達成、樂渡、永惺及妙智。[19]畢業禮當天,除了學佛院的董事及師生外,還有來自各方道賀的大德,如覺光法師、印順導師、優曇法師、明觀老法師、寬慧法師等,嘉賓如雲,自有一番盛況 。


倓老在畢業典禮致詞中特別提到,時代巨輪不斷前進,社會上人心不古,僧團的托鉢、法事、供養等生活,已靠不住了,因此學僧有必要自食其力。例如印經是為他們將來能自立而做的準備。他又勉勵學僧,不要以此為滿足。佛法廣大精微,應當發精進心,自力修學,以期「上報四重恩,下濟三途苦」。[20]
就在第二屆準備招生的時候,倓老開始感到狀態不如以往。無論是體力上,還是精神上,都不足以繼續勝任院長一職;因此他便懇請學佛院的董事會 ,准許他辭職,另選賢能。但當時還有年輕僧人不斷南來求學,而且第一屆尚未畢業的學僧,也要繼續讀下去。大家心裏都不免擔憂,缺少了倓老 ,華南學佛院到底還能走多遠?
[1] 倓虛老法師出生至來港前各種弘法事蹟,詳見《影塵回憶錄》(全二冊),1955年。
[2] 葉恭綽居士(1881-1968),字裕甫,又字玉甫、譽虎,號遐庵、遐翁,廣東番禺人。中國近代政治家、文學家、書畫家及收藏家。葉居士積極護持佛法,於中港兩地佛教事業貢獻殊多。
[3] 廣州光孝寺是著名禪宗古剎,歷史可追溯自晉代。自民國紀元起,寺廟即遭政府及學校機關佔用,先後辦過法官學校、警備司令部、至抗日勝利後情況益加猖獗,光孝寺為廣東省教育廳接管,在原址開辦省立藝專學校。虛雲老和尚與一眾護法居士等發起「維護光孝會」,是為復興光孝寺一事之緣起。參見《廣州藝專非法佔用光孝寺之我聞》,《海潮音》第29卷第2期,1948年,收入黃夏年主編,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第204冊,北京: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,2006年。
[4] 台灣侯坤宏教授在一篇談及1949年前後僧人來港歷程及他們留港期間的生活狀況的論文中,引用倓老弟子大光法師記載,取倓老「是在3月間抵達香港」之說,並在註釋指:「樂渡法師則記為4月4日」。其實大光法師原文乃言農曆三月。倓老從青島來香港事,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的《覺訊月刊》及香港《華僑日報》已刊載詳情。前者有〈倓虛法師過滬飛港〉新聞一則,記「倓虛老和尚,因葉恭綽居士邀赴香港弘法,於4月1日道經上海,⋯⋯於4月3日本會星期講座講演『十法界緣起』。⋯⋯翌晨即搭機飛港云。」足證倓老來港,確是新曆4月4日。參見:侯坤宏〈避風港:1949年前後的香港佛教〉《人間佛教研究》,第 7 期,2016年,頁97-157;〈倓虛法師過滬飛港〉,《覺訊月刊》,第3卷第5期,1949年,頁19,收入黃夏年主編,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》第78冊,北京: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,2008年;〈佛教大德倓虛來港〉,《華僑日報》,1949年4月4 日,第5版。
[5] 〈追思恩師略敍創辦華南學佛院之經過〉,《香港佛教》第43期,1963年,頁21-23。
[6] 〈輓倓公大師〉,《香港佛教》第43期,1963年,頁18。
[7] 參見《倓虛大師法彙》第三編〈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〉,1974年,頁334-335。
[8] 參見《倓虛大師法彙》第三編,1974年,頁329-330。
[9] 〈追思倓公,看破,放下、自在〉,《香港佛教》第43期,1963年,頁53-54。
[10] 關於華南學佛院初期收生人數,一直有兩個版本,分別是二十一及二十人。說二十一人者有倓老〈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.鈞會准予備案由〉中「現已招收學僧二十一名開始上課」,及樂渡法師〈追思恩師略敍創辦華南學佛院之經過〉。後者尤其詳細指出,「前後學僧二十一名,三位老法師,再有廚夫,校役各一名,共二十六人。」然而到了1952第一屆學僧畢業時,倓老在〈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〉中,已更正為「學僧暫定為二十名」、「學僧二十名,本屆畢業者十名」(另見後文)。對此最簡單的解釋是,其中一位學僧開學後退學,不過筆者近日翻閱《道安法師遺集》的日記部分,法師在1950年11月11日記有下列事項:「華南佛學院(註:道安法師每每提及華南學佛院多稱佛學院,純熟手民之誤)死了一個學僧,下午送芙蓉山火葬。」由於缺乏前文後理,我們不能單憑法師日記便斷言此乃二十一人變為二十人之緣故,故法師此說,只能聊備一考。參見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,《道安法師遺集》, 1980 年,第 5 冊,頁416。
[11] 筆者有一照片,借自加拿大湛山精舍,是第一屆學僧、導師、護法居士等攝於弘法精舍大殿前「客廳」(時人稱呼),拍攝場合極有可能與課程開學有關。礙於筆者才識有限,僅能辨認到當中十七人,其餘三位(四位)學僧為誰,還望方家指教。
[12] 《影塵回憶錄》下冊,1953年,頁178-181。
[13] 《影塵回憶錄》下冊,1953年,頁178-181。
[14] 〈啟建冥陽兩利法華道場說明〉,《倓虛大師法彙》第三編,1974,頁328。
[15] 〈蔣維喬〈諦閑大師遺集序〉,《諦閑大師遺集》第一冊,1952年,頁11-13。
[16] 倓虛老法師〈華南學佛院學習印刷情況〉,《弘化月刊》第126期,1951年,頁14,收入收入黃夏年主編,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》第71冊,北京: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,2008年。
[17] 五號鉛字用於註解
[18] 倓老所言月份及日子,皆為農曆。
[19] 一直以來,華南學佛院並未有公佈確實的畢業生名單。文中所列出十名畢業學僧,乃根據大光法師所藏的「香港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師生暨董事合照」辨認。外間多流傳某某法師為華南學佛院(第一屆)畢業生,如智梵法師、性空法師等,若依照倓老畢業典禮致詞中「學僧二十名,本屆畢業者十名」計,未有在合照中持證書者,應不能當作畢業生計算。
[20] 〈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〉,《倓虛大師法彙》第三編,1974年,頁334-335。